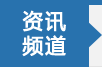“絲綢絲綢,越做越愁。”近日走訪南充絲綢企業,這句話被反復提及。企業負責人說,這是行業當前發展的共性。四川是全國重要的絲綢生產基地,絲綢產業鏈完整。四川綢緞產量居全國第一。南充,有“中國綢都”之稱,重要性不言而喻。“綢都”的絲綢企業在愁什么?應該怎樣為南充甚至四川的絲綢產業發展消愁?
絲價波動頻繁
成本高風險大
對有上百年歷史的老絲綢企業四川南充六合(集團)有限責任公司來說,2018年猶如“寒冬”。“2018年經營情況不是很好,銷售收入下滑10%左右。”其董事長任立榮說。更致命的是,2018年12月31日,占據企業主營業務收入超60%份額的絲綢服裝等終端成品制造環節,控股股東宣告撤資退出。
同是絲綢企業,一江之隔的民營企業四川依格爾紡織品有限公司的日子也不好過。董事長張和才說:“往年銷售收入接近2億元,2018年剛1億元出頭。這兩年生絲價格波動太大。”
2018年上半年,生絲價格最高達到近60萬元/噸。而現在同品級的為40多萬元/噸。短短幾個月,近1/3的價格波動,讓不少絲綢企業望而卻步。“成本太高,風險太大。”張和才說,受價格影響,2018年企業純真絲面料訂單量下降明顯。“訂單從幾萬米下降到了幾百米。”
任立榮說,絲價“過山車”增加了企業生產的風險,2018年六合經營狀況不佳,一半原因源自于此。
盡管絲價漲跌不定,但總體來看,企業家認為,絲綢業整體已進入高成本時代,絲價高企趨勢將長期延續。數據顯示,2018年我國絲綢內銷占比達60%,已成為世界最大的絲綢消費國。旺盛的消費需求,會刺激原材料價格上漲。另一方面,栽桑養蠶的人工成本、土地成本等不停上漲,也必將推高生絲價格。
產業“上強下弱”
市場競爭力弱
成本上漲不可逆。對絲綢企業而言,未來比拼的是誰能更好消化成本。而這也恰恰是南充絲綢企業“愁”的深層次原因。
筆者向多家南充絲綢企業負責人詢問業務構成情況:半成品加工和代工生產占比基本保持在60%左右,其余30%多為絲、綢出口,剩余不到10%才是自有品牌的終端產品。
在各大絲綢企業的銷售展廳,銷售的真絲睡衣、絲巾、床品等,品類、圖案到樣式大同小異。也有一些企業為了降低成本,嘗試研制了一些價格更“親民”的產品,如單面絲綢的床品、枕套等。
終端產品市場競爭力不強的不只是南充絲綢企業,“四川省絲綢產業整體的發展現狀就是上身強壯,下身瘦弱。”四川省絲綢科學研究院院長程明打了一個形象的比方。
絲綢產業的產業鏈特別長,從前端的桑蠶繭到中端的制絲制綢,再到終端的印染、產品設計制作等精深加工,某一環節出問題,整個鏈條就會失衡。而目前,四川絲綢產業的相對優勢主要集中在中端,前端和終端都急需補強。在前端,四川生絲產量僅次于廣西,位列全國第二,生絲質量全國第一。但是算一下細賬:四川栽桑養蠶一年可養5~6批,平均年收入在8000~12000元/畝之間。而在廣西、云南等日照更充足的地區,可養12批左右,收入達14000元/畝左右。面對“后起之秀”廣西,其日照時間長、農村富余勞動力多、出口成本更低等特點,四川想繼續擁有前端優勢并不容易。
在中端和終端,目前四川省80余家規模以上絲綢企業分布在19個市州,絕大多數在制絲制綢的中端領域。南充絲綢企業較為密集,但企業大多依靠代加工生存。“客戶要求較高的印染,我們多是拿去江浙做,做完再拉回來加工。”王尚雪說,如此一來,成本上漲壓力進一步增大,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受影響。
嘗試文旅結合
支持集群發展
為了“活下去”,南充絲綢企業已開始探索消愁之道。一個有趣的現象是,不論規模大小,南充絲綢企業不約而同嘗試了“前店后廠”、文旅結合的模式。
產業要謀求更大發展,集群式發展被南充市政府作為重要抓手。“絲紡服裝產業是南充明確要重點培育的五大千億產業集群之一。”南充市商務和糧食局局長鄭和平說。目前,南充絲紡服裝產業規模接近400億元。如何成長為千億級?在他看來,招大引強,補強產業前端、終端是可行之路。
前端,加大蠶桑農產品多元化開發。比如,嘗試在繭子環節提取處理,加大蠶絲面膜等化妝品、保健品研發制造。終端,則需要引進國內領先的家紡企業等,引發“鯰魚效應”,激發企業真正加強終端產品創新研發。
這個思路,也和程明的想法不謀而合。“四川絲綢產業在2000年左右和江浙差距逐漸拉大,如今國內消費市場蓬勃發展,四川絲綢產業發展又迎來窗口期。”他認為,加大終端環節的招大引強,政府應該在綜合治污等方面集中發力。“能否高水平建設產業園區,集中處理印染等環節的污水廢水處理,讓企業像使用水、電等要素一樣,購買使用污水治理?”此外,四川也應集聚科研優勢發力“無水印染”等行業核心共性技術攻關。
四川絲綢,對行業從業者而言,更多的是輝煌的記憶。四川絲綢如何重獲新生,或許還需要更多新思路。